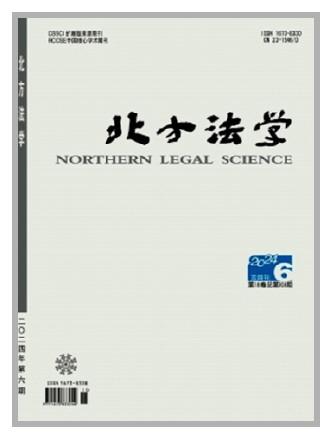
同济大学法学院熊倍羚在《北方法学》2024年第6期上发表题为《个人信息主体同意撤回权的规范定位与冲突协调》的文章中指出: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已经迈入数字时代。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科技的应用在为人们提供高效、便捷服务的同时,也给信息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然而,纵观我国建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体系,可以发现其中涉及个人信息主体同意撤回权的规定数量较少。同意撤回不仅为个人信息主体作出的瑕疵同意提供了纠正路径,还阻断了个人信息处理者继续获取个人信息的有效渠道,防止个人信息处理者以机器学习的方式分析和推测其偏好,避免受到算法操纵。在此背景下,正确解释同意撤回权的规范内容既有利于同意规则的完善,也对进一步实现个人信息主体的信息自决具有重要意义。
同意撤回权与意思表示的撤回和撤销分别在行使对象和溯及效果上存在较大差异,这一分歧表现为同意撤回的性质争议。考虑到同意撤回权是同意规则项下的特殊规范,故对同意撤回性质的判断应以同意性质的判断为出发点。回溯同意规则的理论来源和规范目的,仅以同意规则在适用过程中存在困境为由并不足以否定其作为意思表示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相反,将同意视为意思表示在个人信息保护领域贯彻意思自治精神的重要体现,也符合“同意”自产生之初所蕴含的根本宗旨。由此,同意撤回本质上是个人信息主体对其先前持续性授权的撤回意思表示,可适用意思表示的相关规则。
厘清行使条件是研究同意撤回权的核心内容。就权利主体而言,除成年人是同意撤回权的当然适格主体之外,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未成年人以及不同行为能力层级的成年人,应当在充分尊重两类群体意愿和信息主体地位的原则基础上采取与之相协调的同意撤回模式。就适用对象而言,由于同意撤回符合“纯获利益”以及“与年龄、智力相适应”的特质,8岁以上未成年人不宜适用监护人同意撤回模式。替代同意人为欠缺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撤回同意时须受到限制。
就同意撤回与法定许可的关系而言,两者并存时必须择一适用。当个人信息主体撤回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同意时,这一行为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合同的履行以及相关责任的界定。对此,需要厘清涉及个人信息合同交易的内部结构。涉及个人信息的合同交易主要包括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与基础合同两个部分,前者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调整对象,后者则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当个人信息处理行为涉及合同交易时,个人信息主体是否享有同意撤回权须视其提供个人信息的合同义务性质而定。尽管个人信息处理与基础合同相互独立,撤回同意仍可能导致合同的变更或解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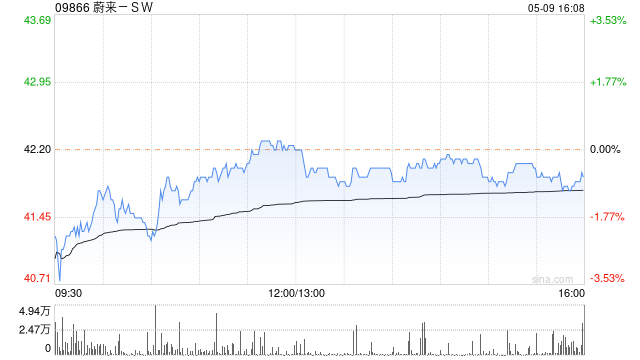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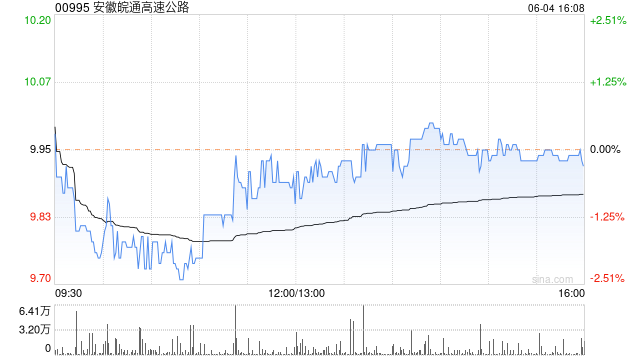

发表评论
2025-01-13 03:12:09回复
2025-01-13 04:25:10回复
2025-01-13 09:12:48回复
2025-01-13 09:33:28回复
2025-01-13 03:28:02回复
2025-01-13 04:20:46回复
2025-01-13 08:06:18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