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姬黎明
在中国历史上,公元3世纪的西晋政权是一个腐败、混乱而短命的王朝,但却是律学繁荣发展的重要阶段,出现了一批律学大家,可谓群星灿烂,刘颂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刘颂曾为廷尉,不仅执法如山,人们将他比作西汉的张释之,而且对法制有许多深刻而独到的思想。他明确提出:“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意思是说:审理判决案件时,应当以法典律令的明文规定为依据;如果没有明文规定,则参照总则篇中的定罪量刑原则进行处理;若律令正文、总则中都没有规定,则不能定罪。这一思想被后人称为“援法断罪”,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罪刑法定”原则相似,但比西方早了将近1500年。
据《晋书·刑法志》记载,晋惠帝(就是问饥饿的老百姓“何不食肉糜”的司马衷)年间,时任三公尚书的刘颂呈上一篇《刑法疏》。这篇奏疏针对当时“法渐多门,令甚不一”的混乱现象,通过鞭辟入里的分析论证,提出“君臣之分,各有所司”,即君主立法,主管大臣解释法律,一般官吏严守法律。就司法职权分工来说,“主者守文”,即要求司法官吏在执法过程中严格依据法律条文断案,不得随意解释或偏离法律文本;“大臣释滞”,即对于法律条文中难以理解或存在争议的部分,由主管大臣进行解释和疏通;“人主权断”,即对于特殊案件或法律条文无法涵盖的情况,由人君进行最终裁决。刘颂认为“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反对人君随意立法改制、随意干涉司法,反对法外施恩,反对为求尽善而迁就舆论、伤害法律,特别指出“出法权制,指施一事”,虽然可能合乎人情、舆论,从表面上看很痛快,实则“恒得一而失十”,就会破坏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造成灾难性后果。他提出“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反对官吏“牵文就意”,反对为了迎合上级而随意执法,反对脱离法律去搞“看人设教”“随时之宜”,认为那样就会使立法权被执法官吏僭越,导致法官立法,造成“法多门、令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事同议异,狱犴不平”等局面。他放言高论“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大声疾呼“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措思于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恒全”。其目的就是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刘颂提出了援法断罪思想,强调司法判决必须在法律之内而不能在法律之外找依据,法无明文规定就一概不能定罪。
刘颂援法断罪思想是他个人近40年司法实践经验和对法律精神执着坚守的理论概括。刘颂不仅在多个任上都创造了严格依法办案、伸张正义的经典故事,而且直言敢谏,他对法制的真知灼见集中体现在他的奏疏中。史书称赞他“在官严整,甚有政绩”“上疏论律令事,为时论所美”。面对司马氏统治带来的政治危机,刘颂认为只有君臣共同遵纲守法才能补救,主张纲举网疏和援法断罪,“诛大罪”“赦小过”。
刘颂援法断罪思想是在西晋律学繁荣发展的背景下,清醒的官僚士大夫提出的较为理性的法律主张。西晋在官府开设了“律学博士”,律学从经学中分离出来。《晋律》就是在律学日趋成熟的基础上完成的,矫正了律令混用不清的弊端,正律的地位提升,非依律不能定罪。律学家们认识到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就是维护统治集团的根本、长远、全局利益,因而试图以法律手段对皇权的绝对性加以限制,对豪强大族的恣意妄为予以打击,对官吏的司法擅断加以防范,从法制领域“主者守文”、制约权力这个侧面阐释和展示了魏晋风度,奏出了那个时代法制文明的强音。
刘颂援法断罪思想也是对春秋战国法家“一断于法”、秦汉时期“法令一统”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至唐时期,这一思想已经上升为法律制度,成为一项司法责任。唐律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这是我国古代关于援法断罪最简明、最具代表性的法律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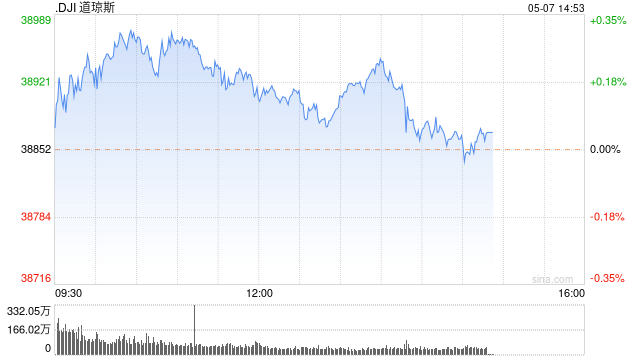







发表评论
2025-01-23 09:14:03回复
2025-01-23 16:57:19回复
2025-01-23 17:15:09回复
2025-01-23 09:51:37回复
2025-01-23 17:10:59回复
2025-01-23 16:23:43回复
2025-01-23 07:59:16回复
2025-01-23 15:37:54回复
2025-01-23 16:38:25回复
2025-01-23 12:20:15回复
2025-01-23 11:02:16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