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杨幸芳
近日,“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利保护与创新发展”论坛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该论坛作为国家版权局第八届中国网络版权保护与发展大会的分论坛之一,深入探讨了网络环境下广播组织权的相关问题,旨在加深业界对广播组织权利保护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凝聚对广播组织权的共识,促进广电产业和版权产业的创新发展。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知识产权创新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陶乾在该论坛上作了题为《新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的修改及未来完善建议》的主题发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知识产权创新与竞争研究中心主任 陶乾)
陶乾首先介绍了我国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修改的具体内容。为应对数字时代广播组织权保护面临的挑战,2020年著作权法修订时对第47条广播组织权进行了四处修改,第一是在广播组织转播权中增加了“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以便与作品广播权规则相一致,从而能够将网络实时转播纳入到广播组织权的控制范围;第二是在广播组织录制与复制权中删除了“在音像载体上”这一要求,从而与作品复制权规则中新增的“数字化方式”相一致;第三是新增广播组织信息网络传播权,从而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规则相一致;第四是新增了对广播组织行使权利的限制性规则。
当广播组织权增加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之后,该权利是不是会与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录像制作者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产生重叠甚至冲突呢?陶乾认为,这四项权利产生的原因不同,权利的客体亦不同,因此,每一项权利相互独立,每一项权利项下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不重叠。广播组织权的客体是信息流,信息流上的内容是音视频节目,信息流是以信号为传输手段。法律为广播组织设定邻接权,旨在保护其在形成、传输和播放信息流过程中进行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资回报。“信息流”说可以妥适地调和学术界对于“信号说”和“节目说”之间的分歧。
著作权、表演者权、录音录像制作者权、广播组织权这四项权利虽然相互独立,但又存在关联。围绕一部作品的创作与传播,这些权利的产生有先后之分。作者创作作品产生著作权;接着,表演者表演作品产生表演者权;然后,对表演者的表演进行录音录像,产生录音录像制作者权;最后,广播组织制作广播电视对录音录像进行传播,产生广播组织权。当在后权利的客体中包含着或者承载着其他主体的在先法定权利时,其权利行使必然受制于其他主体在先权利的牵制,但这种牵制并不影响该权利存在的独立性。由于广播组织权产生顺位居后,故其行使不得影响、限制或者侵害他人行使在先已经产生的著作权、表演者权和录音录像制作者权,这是法理使然,第47条第二款专门就此进行规定实无必要。与此类似,录音录像制作者权的行使不得影响、限制或者侵害在先产生的著作权和表演者权。
针对现行著作权法对广播组织权的规定,陶乾认为有以下三点需要进一步完善。第一,将立法语言从“有权禁止”恢复为1990年著作权法的“有权许可”“禁止”和“许可”是权利的“一体两面”,广播组织权作为一项著作权法规定的财产性权利,对外许可是权利人行使支配权能的应然之义;第二,修改著作权法第49条第三款对技术措施的定义,将广播、电视增加到技术措施的保护对象中;第三,在刑法中明确对广播组织权的刑事保护,以便与著作权法第53条规定的能够导致刑事责任的侵权样态保持一致。对于破解加密措施的盗播行为,将其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17条(六)对破坏技术措施的规定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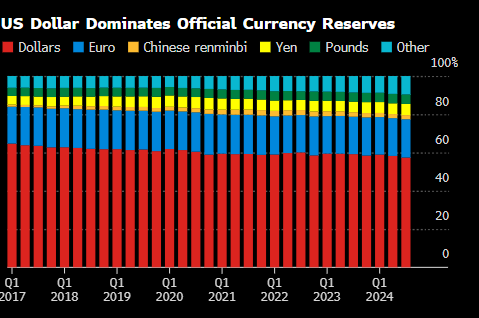






发表评论
2024-12-25 06:50:50回复
2024-12-25 06:42:35回复
2024-12-25 11:49:32回复
2024-12-25 02:06:51回复
2024-12-25 07:18:00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