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仁文
日本学者冈田朝太郎在百年前的京师法律学堂演讲中,曾深刻指出:“一国司法制度之良否,关系于实体法(刑法、民法)者半,关系于形式法(民、刑诉讼法)者亦半。”我国近代法律改革的先驱沈家本在论及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时,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窃维法律一道,因时制宜,大致以刑法为体,以诉讼法为用。体不全,无以标立法之宗旨;用不备,无以收行法之实功。”这些观点穿越时空,至今仍对我们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们不仅强调了实体法与程序法在构建国家法治体系中的基础性作用,也揭示了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支撑的密切关系。刑法与刑事诉讼法正是这样一组关系,它们如同天平的两端,既密切关联又相互制衡,共同筑成刑事法治的基石。
追溯至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早期,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往往一体共生。例如,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与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均是实体法与程序法融为一体的法典。随着社会的日益复杂和法律体系的不断演进,刑法与刑事诉讼法逐渐从早期的合体形式中分离出来,发展成为彼此相对独立的法律体系。1808年,法国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独立的《刑事诉讼法》,此后,德国等欧洲国家纷纷效仿法国制定独立的刑事诉讼法典,逐渐形成了实体法与程序法相分离的立法模式。
中国的法律演进也体现出类似的进路。从周代的《吕刑》、战国的《法经》,直至《唐律》及其后封建社会的历朝刑律,都是刑事实体法与刑事程序法合二为一。1911年1月,晚清政府制定的《大清刑事诉讼律(草案)》(该草案未及正式颁行),应是我国刑事程序法独立成典的最早尝试。此后,北洋政府时期的《刑事诉讼条例》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刑事诉讼法》,皆采用了刑事程序法从刑事实体法中分离的立法模式。
与法律体系的变迁相对应,刑事法学科亦大致经历了同样的发展轨迹。1764年,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一书的出版,标志着近代意义上刑事法学科的诞生。但该书不仅涉及犯罪定义、刑罚适用等刑法核心议题,也涉及逮捕、审判方式等刑事诉讼关键内容。此后,随着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分立以及知识领域的不断分化,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分别获得了独立的学科地位。尽管如此,由于实体与程序在实现刑事正义中的互相依赖,也注定了研究刑法的人必须研究刑事诉讼法,同样,研究刑事诉讼法的人也必须研究刑法。正因此,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进行融合研究在域外是一个普遍现象,许多学者既是著名的刑法学家,也是著名的刑事诉讼法学家。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取得蓬勃发展,特别是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在法治重建中率先出台,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的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如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和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的分别组建,以及各教学科研单位分别设立刑法学教研室(研究室)和刑事诉讼法学教研室(研究室),并分别培养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导致两个专业间的隔阂愈来愈深。尽管近年来储槐植先生提出的“刑事一体化”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刑法学界与刑事诉讼法学界的沟通,也取了一些成果,但囿于我国法学教育和学科设置的传统框架,实质性的进展不明显。
当前,在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的关系上,有以下两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重视:一是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不同步,带来两法间的龃龉。1979年,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本是同时颁布的,但后来刑事诉讼法分别于1996年、2012年和2018年进行过三次修正,而刑法则是在1997年进行过一次大的修订后,又先后进行了13次修正(包括一个单行刑法和12个刑法修正案)。由于修订频率与修订时间不同步(并不是说修订频率要绝对同步,但能同步的要尽量同步),导致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出现彼此不一致甚至互相冲突的现象。二是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对域外理论各有青睐,带来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立法的不同影响。
陈妍茹博士所著《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及适用研究》一书,是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交叉研究领域的又一有益尝试,我认为该书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兼顾宏观与微观。作者在阐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相互作用的基础上,聚焦于刑事审判的核心环节——定罪与量刑,研究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事实认定、证据运用以及法律适用等方面的交错适用关系,并以非法持有枪支罪等为例,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刑法各罪与刑事诉讼的关系。其次,区分应然与实然。作者强调了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在应然上的协同关系,也列举了两者在实然上出现的种种冲突和矛盾。再次,注重定性与定量。作者收集了大量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作为研究样本,以此为切入来探讨定罪与量刑中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关系。
当前,我国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正处在一个活性化的时代,刑法学和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也空前活跃。时代呼唤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深度融通,呼唤刑法学与刑事诉讼法学的通力合作。期待该书进一步激发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为更好地实现刑事正义这一崇高志业不断添砖加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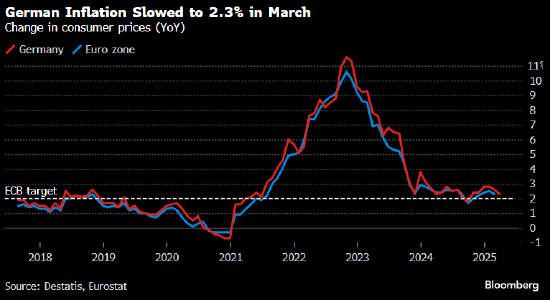

发表评论
2024-12-14 00:15:12回复
2024-12-14 10:25:44回复
2024-12-14 00:31:55回复
2024-12-14 04:48:23回复
2024-12-14 07:09:26回复
2024-12-14 01:02:20回复
2024-12-14 08:03:00回复
2024-12-14 03:11:33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