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溯
在当下关于刑民交叉问题的探讨中,对于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关系,形成了两种主要学说,即互斥说与并行说。
“互斥论”的既存困境
(一)“互斥论”的立场设定
在形式逻辑的范畴中,存在着所谓的择一连结,其以非a即b的陈述形式呈现,a与b同时仅可能有一者成立。为了避免处理复杂的竞合问题。因此,立法者或者司法者往往倾向于通过立法或者解释的方式在构成要件中加入相互排斥的构成要素,从而使得两个构成要件形成互斥关系。当前,在我国理论与司法实践中,围绕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存在着诸多如何界分二者的讨论。这种界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在预设二者互斥关系的基础上展开的,即认为某一或者某些构成要素仅为民事欺诈或者刑事诈骗所具备,由此得以区分二者。
(二)“互斥论”的方法困境
这一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标识出处于矛盾关系的构成要素,从而提醒司法者在司法审查时着重关注特定构成要素,避免刑事处罚范围的不当扩大。然而,这一思路的根本问题在于背离了犯罪审查的逻辑:
其一,这一思路预设了行为人要么构成民事欺诈,要么构成刑事诈骗。学者指出,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成立边界完全重合,且能够通过民事调整的有效限度逆推诈骗罪的成立范围。这一思路即忽略了行为人连民事欺诈也不构成的可能,也忽略了行政欺诈的可能,从而导致审查过于烦琐或者出现不当入罪。
其二,这一思路忽视了犯罪构成要件审查所固有的检验顺序,当前的“互斥论”的思路,在预设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互斥关系后,又尝试找寻部分特殊的构成要素作为区分二者的标准,实际上是将特定的构成要素从犯罪审查步骤中剥离出来,从而打乱了诈骗罪成立既有的检验顺序。
其三,这一思路将构成要件以外的要素作为诈骗罪的成立依据。“互斥论”预设了行为要么构成民事欺诈,要么构成刑事诈骗,因此,理论与司法实践可以借助于刑法体系之外的标准来对行为是否构成刑事诈骗进行逆推,救济可能性便是其中代表性观点。但这一观点实际上忽视了刑法最后手段性所指向的主体,而将对国家刑罚权的限制转换为对被害人的限制,从而致使被害人不得不在穷尽救济可能之后才能诉诸刑法手段。
(三)“互斥论”的具体质疑
第一,单一区分标准之质疑。首先,非法占有目的的正当性疑问。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区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标准,是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诈骗犯罪所共有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为前提的。然而,这一前提并不存在天然的正当性。从我国立法与司法解释来看,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构成要素,仅被明文规定于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等特殊诈骗犯罪之中。因此,在非法占有目的本身作为诈骗罪的主观构成要素就存在疑问的情况下,再将其从金融诈骗与民事纠纷的区分标准拓展为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区分标准,就无异于“沙上建塔”。
其次,非法占有目的的肥大化趋势。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区分狭义的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单一标准,固然为司法实践区分二者提供了简明的操作指南,但却使非法占有目的承受了过多的功能期待,进而使得欺骗行为、财产损失等客观构成要素的内容借助于对主观目的的客观推定被放置于非法占有目的中。
最后,非法占有目的的碎片化状况。当前对于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虽然关注到现实素材的多样性,但却未能整合为统一整体,这使得理论和实践为了应对具体问题而不断将特殊情形纳入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之中。然而,不同视角的累加并非进步,反而进一步导致构成要件符合与否的判断丧失明确性与安定性。
第二,综合区分标准之质疑。相比于单一标准,综合标准尝试借助多个构成要素来区分二者,释缓了单一构成要素的压力,但是受困于“互斥论”的视角,其仍具有不可忽视的漏洞。
倘若认为三组区分标准在界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时共同发挥作用,即认为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在三组构成要素上均存在差异,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评价漏洞的产生。例如,对于一个指向整体事实的欺骗行为,其并未达到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的程度,从而无法构成刑事诈骗,但与此同时,由于其指向了整体事实而非个别事实,也不能构成民事欺诈。
倘若认为上述综合标准仅仅是平行关系,即相互补充的作用。由于,诈骗罪构成要素的判断存在逻辑上的检验顺序。各标准均处于或然性的地位不仅意味着在诈骗罪的构成要件审查中采取了耦合式的思路,并且这一思路也违背了“子项不相容”的形式逻辑要求。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并行视角
归根结底,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如何准确地划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限,而在于自始我们便无必要将二者并置讨论。
(一)基于犯罪审查的论证
在与“三阶层”犯罪论体系相适应的犯罪审查过程中,倘若行为人的行为可能符合多个构成要件,司法者对于每一个构成要件都应当单独地加以审查。在某一构成要件的审查过程,其结论仅能为行为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此构成要件,而不可能从中得出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其他构成要件与否的结论。
“互斥论”的问题在于:通过建构两个构成要件之间的互斥要素,将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转化为单一互斥要素的具备与否的问题,致使犯罪审查的过程被压缩为单一或者部分构成要素的审查过程,并通过建构互斥要素,将应当分别进行的两次不同构成要件的审查放置在同一审查过程中进行。如果暂且忽视不同诉讼程序之间的区隔,当一行为可能构成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时,那么通常而言,应当首先审查不法程度更高的刑事诈骗的构成要件。因此,在后的民事欺诈的审查结论并不可能回溯的影响刑事诈骗的审查。当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界分标准无法在犯罪审查过程中得以体现时,围绕二者关系的讨论实际上已然偏离了构成要件的功能所在。
(二)基于民刑交叉的论证
对于涉及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罪界分的案件,其属于由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同一法律关系,只能归属于刑事或民事范畴,但刑、民违法性难以定性的案例,从而归属于前述同一法律事实引起的刑民交错案件。对于此类案件的诉讼程序,当前司法机关主要采取“先刑后民”的思路,并存在着“一体化模式”与“移送模式”两种处理模式。在不同模式中可以看出,在诉讼程序上,对于行为人行为是否构成刑事诈骗的审查,始终先于对行为是否构成民事欺诈的审查,正与“并行论”下对于行为符合何种构成要件的审查思路相契合。而从案件审理结果来看,倘若行为人被判构成刑事诈骗,根据司法解释,仅要求在后的民事诉讼的审判者直接认定刑事判决已决事实,也肯定了民事诉讼作出法律评价的独立性。倘若行为人被判不构成刑事诈骗,原民事纠纷当事人需要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民事纠纷的解决,但与“不告不理”原则相适应,并保证了当事人选择请求权的自由。
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并行论”的具体展开
我们需要重新重视诈骗犯罪的每一构成要素所具有的限制可罚性范围的意义,而无需依赖于单一构成要素。
对欺骗行为而言,诈骗罪作为结果犯,意味着客观归责理论能够应用于诈骗罪的构成要件研究之中。因此,行为人的欺骗行为必须指向被害人的财产损失,并且达到足以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且造成财产损失的程度;对错误认识而言,需要考察被害人是否因行为人的欺骗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以及被害人的错误认识与欺骗行为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联性;对财产损失而言,应当将被害人外部化、客观化的交易目的纳入考量之中;对于非法占有目的,其征表了诈骗罪的行为不法,需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处于获利目的、所追求的财产利益是否与财产损失具有同质性以及行为人所追求的财产利益在客观上是否为不法。
(原文刊载于《政法论坛》2024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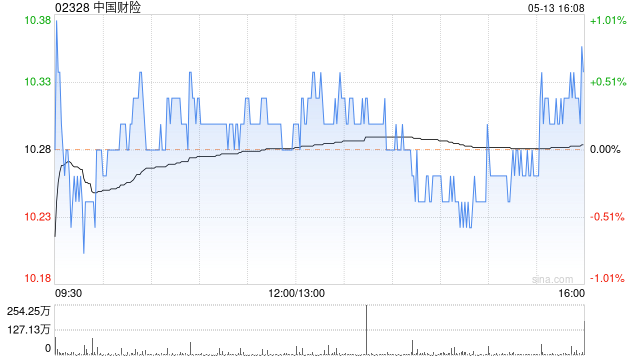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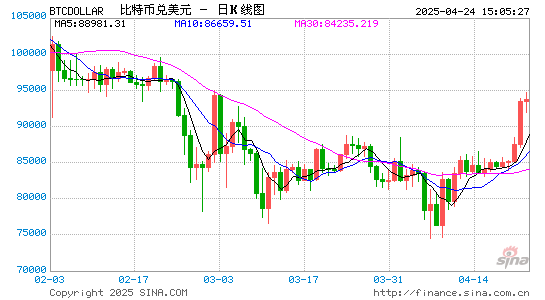
发表评论
2024-12-09 08:14:34回复
2024-12-09 11:12:47回复
2024-12-09 18:17:51回复
2024-12-09 14:56:43回复
2024-12-09 13:00:08回复
2024-12-09 09:46:10回复
2024-12-09 16:17:36回复
2024-12-09 09:57:02回复
2024-12-09 06:54:57回复
2024-12-09 08:30:12回复
2024-12-09 13:32:05回复
2024-12-09 15:14:47回复
2024-12-09 14:10:35回复
2024-12-09 17:28:41回复
2024-12-09 08:07:29回复
2024-12-09 08:46:03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