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金林
贿赂犯罪法益学说会对刑法的规制范围、定罪量刑、涉案财产处理等问题产生重大影响。近年来,我国刑法理论界掀起了研究贿赂犯罪法益的热潮。这些讨论推进了该问题的精细化研究,但过分受制于德国刑法理论的基本框架,很难全面回答从我国特有的制度土壤中生发的问题。
对贿赂犯罪法益既有学说的批判
(一)贿赂犯罪法益确定的基本要求
根据法益确定的一般原则及其与贿赂犯罪的关联性,贿赂犯罪法益的确定应通过以下检验:
第一,循环论证检验。也即,必须用独立于刑法规定和司法惯常做法的法益来指导立法的解释、限定其适用范围、检验司法实践。
第二,终极追问检验。法益应和人类自由、和平共存的基本条件直接建立联系,因为任何中间概念都可能导致可罚性范围不当地扩大或缩小。
第三,损益关系与法益侵害程度检验。法益必须足以阐明构成要件行为对谁的什么利益造成了何种程度的侵犯,要能对犯罪不法作质与量的判断,区分危险与实害,解析出影响不法程度的量刑情节。
第四,系统、周全性检验。贿赂犯罪的法益理论,要尽可能全面地对贿赂的不法内容作系统、全面、合理的说明,合理解释枉法与非枉法等因素对惩罚范围和程度的影响。
(二)以不可收买或交易性为中心的观点
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或不可交易性的观点,具有以下缺陷:第一,不可收买性是一种规范性建构,不具有对规范进行实质解释或限缩的功能。第二,根据不可收买性的逻辑,只要职务与金钱形成对价关系即具有可罚性,因而无法解释行贿罪等犯罪中“不正当利益”的限制。第三,难以解释不法的程度,因为“不可收买性”只有违反与否的区别,没有程度之分。
(三)以公正性为中心的观点
首先,职务行为的公正性或公务的纯洁性难以解释不以不正当的职务行为为要件的非枉法型受贿。其次,公正性说难以解释刑法对行贿处罚的限制,因为按照该说,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且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行贿人,也参与了对公正性的损害,不能作无罪处理。最后,公正性说难以解释商业领域的贿赂犯罪,因为在市场领域,法律尊重私人产权和自由,只要行为没有损及产权所有者的利益,就属于市场允许的行为。
(四)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说
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说也不具有合理性。本质上,公职的不可谋私利性是一种宽泛的道德要求,无法有效提炼出贿赂犯罪的不法内容,不能区分犯罪、违法、违纪以及完全值得鼓励的行为。该观点也不能解释斡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行贿中“谋取不正当利益”的限定。该观点还可能导致贿赂犯罪判断重心的不当转移,因为根据该说,受贿罪是单一的行为犯,实行行为是获取财物的行为,这会使得贿赂犯罪的既遂时点提前到收取钱财之时,不利于鼓励行为人中止犯罪。
(五)以信赖为后缀的法益学说
以对特定内容的信赖作为贿赂犯罪法益的学说也难以成立。信赖可能有两种形式:一是民众对特定对象应当如何行动的期待,二是民众对特定内容相信与否的心理事实。前者无异于民众对特定对象遵守规范的要求,不能通过循环论证检验。后者无法通过终极追问的检验,民众的信赖虽有利于公共行政行为的展开,但公共行政及其指涉的具体利益才是终极的保护目的。以信赖为内容的法益还可能导致犯罪圈的不当扩张。
贿赂犯罪法益的具体化及其应用
将贿赂所包含的行为类型与人类自由、和平共存的基本条件联系起来,可将当前进入“贿赂”这一概念中的行为分为以下几种类型进行处理:
(一)第三人利益侵犯型贿赂犯罪及其应对
贿赂犯罪的第一种可能性,是行贿人和受贿人共同损害第三人利益。如果没有贿赂发生,与行贿人处于利益冲突关系下的第三人,可获得更多的利益或遭受更少的损失。这种类型的贿赂不仅包含事前的枉法型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在事后受财的心理期待下实施枉法行为的,也能构成第三人利益侵犯型贿赂犯罪。斡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是财物收受者推动的侵犯第三人利益的滥用职权。与枉法型受贿对应的行贿,本质上是对第三人利益侵犯的教唆或帮助犯。第三人损害型贿赂犯罪的量刑,应参考其损害利益的性质、损害程度、行为人应承担的责任份额等。
(二)敲诈勒索型贿赂犯罪及其处理
贿赂包含的第二种法益损害类型,是行贿人为其原本应得的利益而提供贿赂。这种状况下行贿人的总体利益因贿赂的发生而减少,是事实意义上的受害人。成立敲诈勒索型受贿,需综合考虑以下因素:
第一,职权的性质。公职人员的职权滥用构成了一般公民难以回避的危险,这种权力可以成为勒索的手段。商业贿赂中,双方的法律地位通常一般是平等的,“不进行市场合作”的威胁通常不足以构成“胁迫”。
第二,行贿人享有仰赖于受贿人职务的正当利益。这里的正当利益,可以是内容明确、与具体职务行为有清晰对应关系的利益,也可以是确定存在但具体内容还不明确的利益。
第三,财物收受方对财物提供者的制约程度。斡旋受贿、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描述的行为一般并不足以解释成对相对人的胁迫,不能成立敲诈勒索型贿赂。
第四,财产交付的时间。在相对人获得正当利益之前,有充分理由将职权行为认定为敲诈勒索的手段。如果相对人已经获得了正当利益,由于其合法利益不再受职权行为制约,此时收取相对人财物的行为原则上不成立敲诈勒索型受贿罪。
敲诈勒索型受贿本质上是财产犯罪,衡量其不法程度的主要因素是财产数额。这种情形下的“行贿人”是受害人,有权要求勒索者返还“贿赂”。
(三)第三人利益侵犯型贿赂与敲诈勒索型贿赂的竞合
以上两种情况可能出现竞合,即“行贿人”不提供贿赂则难以保障自己的正当利益,提供贿赂又可能损害第三人利益。对此,应结合紧急避险的条件,具体判断“行贿人”提供财产的性质。
在负责具体事务的国家工作人员“勒索”贿赂的前提下,正式的救济途径通常并非是与“行贿”同样有效的保护正当利益的方法,一般不宜否定避险的必要性。只要“行贿人”没有现实地获得不正当利益,因行为具有“避险”的性质,即便认为其“行贿”超过了必要限度,也不可能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最多构成“避险过当的未遂”,不值得处罚。
这种情形下的受贿方具有敲诈勒索和第三人利益侵害的概括故意,究竟构成哪种类型的受贿,应根据事后查明的职务行为的法律属性来确定。
(四)欠缺充分法益关联的纪律违反型贿赂及其应对
除第三人利益侵犯型和敲诈勒索型受贿之外,还有处于中间形态的“贿赂”,即既无证据表明贿赂引发或促进了枉法的职务行为,也不存在认定敲诈勒索基础的贿赂收受。其中,难点是没有明确请托事项的感情投资型贿赂。
在这种情形下,由于请托人没有具体的请托事由,财产往来就只会触及抽象的廉洁性,或形成“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遥远的、抽象的危险,这种危险不足以匹配受贿罪的责任与刑罚。对这类行为,只应以纪律处分规制。
(原文刊载于《中国法学》2024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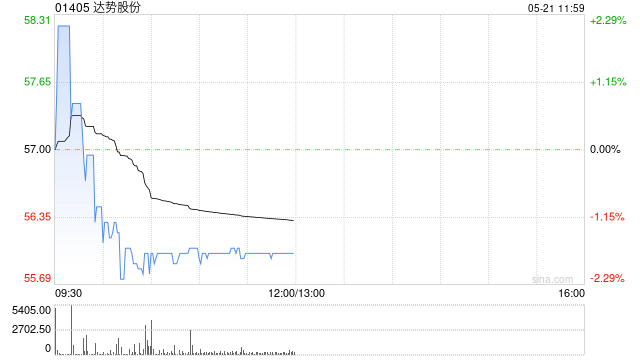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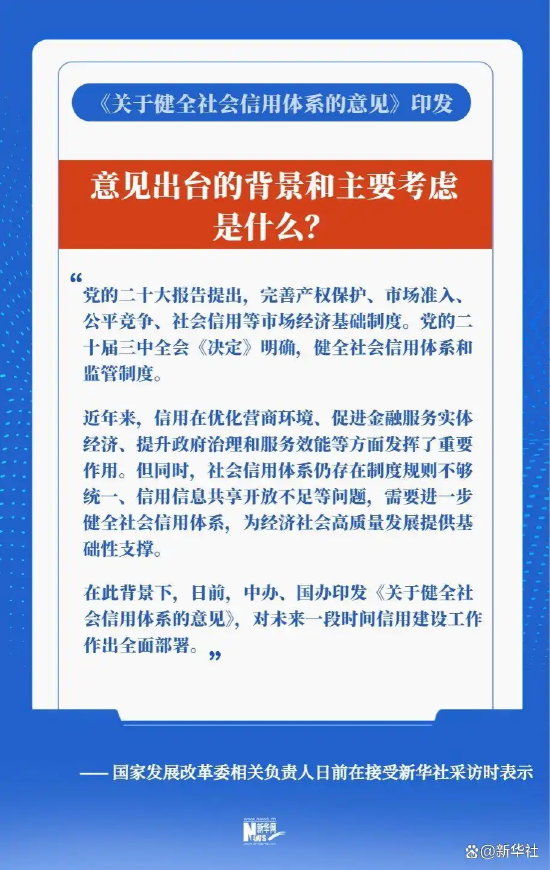




发表评论
2024-12-02 14:32:09回复
2024-12-02 04:43:55回复
2024-12-02 06:34:56回复
2024-12-02 07:24:30回复
2024-12-02 11:50:30回复
2024-12-02 13:24:51回复
2024-12-02 03:57:22回复
2024-12-02 09:24:22回复
2024-12-02 04:25:00回复
2024-12-02 03:56:43回复
2024-12-02 12:51:54回复
2024-12-02 10:17:19回复
2024-12-02 09:34:02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