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黎明
据唐代杜佑所著《通典》记载,西汉景帝时期,廷尉上报了一桩案件:犯人防年的继母陈氏杀害了防年的父亲,防年因此杀了陈氏。按照汉律,杀害母亲应以“大逆罪”论处。景帝对此判决存疑,当时年仅十二岁的太子刘彻(后来的汉武帝)在旁,景帝便让太子发表意见。太子回答:继母虽名义上等同于母亲,但地位实际上不如生母,只是因为父亲的缘故才被视作母亲。如今继母行为恶劣,杀害了防年的父亲,从她动手杀人之日起,作为母亲的恩义便已断绝。此案应按照普通杀人罪论处,不应以“大逆罪”定罪。景帝采纳了太子的意见,参与讨论的官员都称赞这一判决合理。
秦朝的严刑峻法并未带来长治久安,反而加速了其灭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亡教训,从刘邦到汉景帝一直秉持无为而治、休养生息的国策,虽然创造了“文景之治”,但盛世下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汉武帝继位后,不甘在黄老之学的余韵中碌碌无为,决意破旧立新、积极进取,确立了“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治国方略,推崇儒家经典,设立五经博士,建立太学,察举中新增“明经”科。这些“明经”政策及其举措,使先秦儒学发展为汉代经学。经学脱胎于儒学,但不同于儒学,它化用了道家“道”的概念,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汲取了墨家“天志”等思想。经学通过发展“大一统”等理论,为中央集权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既约束百姓服从皇权,又以“天道”限制皇权。儒学发展为经学,不仅重塑了大汉精神灵魂和思想文化格局,而且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提供了理论基础。儒家伦理通过经学渗透到社会各层面,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在儒学发展为经学的过程中,董仲舒是一位关键人物。他以“天人感应”说为哲学基础,构建了完整的德主刑辅理论体系,对法律进行了儒家伦理化改造,推动了礼法结合。董仲舒主张以《春秋》解释法律,并直接用于决狱,强调原心定罪、本事原志,将主观动机纳入法律评价体系,以儒家伦理重塑司法价值标准,得到汉武帝认可。汉代法律把继母“拟制为母”,但未在法律上区分继母与生母的不同地位,也未规定继母与继子女法律关系的解除条件。在这一案件中,太子刘彻以儒家经典诠释“继母”的伦理内涵,弥补了法律条文规定的不足。清代沈家本在《历代刑法考》中引用并分析了防年杀继母案,指出:“此议以继母之恩因父而立,父死则恩义已绝,与常人同科。盖权时之变,不拘常律,深合《春秋》原心定罪之义。”而春秋决狱具有两面性,既有利于天理国法人情的统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司法权的滥用;又容易带来司法断案中的任意比附,以礼代法,破坏法律的统一性和确定性。随着中华法系代表作《唐律疏议》的问世,从立法上实现了“一准乎礼”,春秋决狱也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汉武明经”并不排斥法律,而是给冰冷的法律披上儒家温情的外衣,给严酷的司法活动涂上仁政的色彩。实际上,汉武帝本人崇尚的是“外儒内法”“霸王道杂之”,既承秦制又力矫秦专任刑罚之弊。“汉武明经”后所形成的汉家制度深远影响了后世的立法和治理,塑造了中华法制文明的鲜明特质。历史经验表明,既要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又不能把法律与道德相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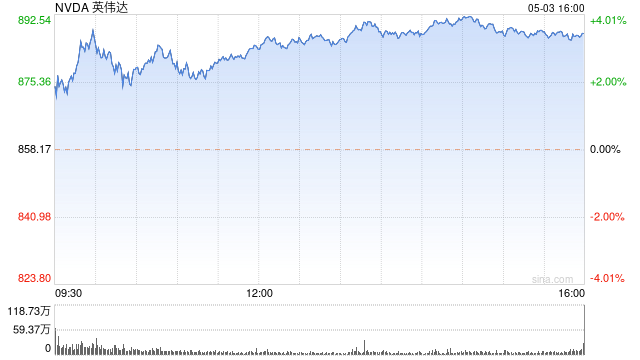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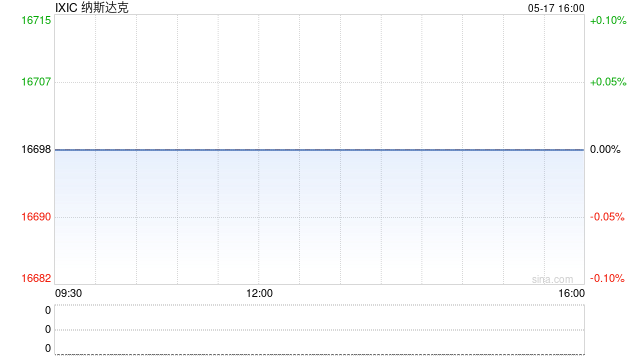

发表评论
2025-02-18 08:41:20回复
2025-02-18 03:02:10回复
2025-02-18 08:37:38回复
2025-02-18 00:13:54回复
2025-02-18 03:27:45回复
2025-02-18 03:36:09回复
2025-02-18 04:31:22回复
2025-02-18 04:30:14回复
2025-02-18 05:37:39回复
2025-02-17 23:20:51回复
2025-02-17 23:32:57回复
2025-02-18 08:12:25回复
2025-02-18 06:25:38回复
2025-02-18 08:07:13回复
2025-02-18 07:58:49回复
2025-02-18 00:53:18回复
2025-02-18 07:37:38回复